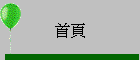
科技社會中社會學研究者的責任(初論)
南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蘇健華
Edward Tenner在其著作《科技反撲-萬物對人類展開報復》中提到若不警覺,我們所日益依賴的科技新興產物將為人類帶來惡果,他認為「報復的效果」多是因為科技本身及其相關系統的複雜程度增強後所帶來的,他提到產生報復效果的主因在於人們對於「更多、更好、更快」的崇拜。[1]
對社會濫用科技的悲觀看法早已存在,早在1920年,捷克的劇作家Karel Capek於其創作的戲劇《R.U.R》(Rossum’s Universal Robots;意指「羅森的萬能機器人」)中創造了「機器人」(Robot)[2]一詞,劇中描述著:工廠中一個生產機器奴隸讓人們從勞役中解脫出來,由於它的作用,人們將它不斷地增多,且在改良之中讓它的智能不斷提升;很快地,在數量上機器奴隸超越了控制他們的主宰,也就是人類,於是它們更被用於戰爭的士兵使用;最後,機器人發起革命,人類在結局中被消滅。有趣的是,這位創造機器人現代概念的作者預期機器人會消滅人類。
對機器人預言家來說,未來是不可思議的豐饒領域,他們預言人類的未來將相當美好,但也可能十分可怕。昇陽電腦公司(Sun Microsystem)的共同創建人Bill Joy相信,若人類不開始著眼於本質上安全的科學與技術控制,那麼現今一些先進的科技都可能會危及人類的安全、動搖人類在物種位階上制高點的相對安全位置。新型智慧機器的科技想法讓Joy有著這樣的想法:對人類目前的成熟度而言,這些科技太先進了。[3]即使是機器人主宰世界的時代仍未來臨,Joy更擔心的是人類可能使用資訊時代的科技對付彼此。在上一個世代,人類的威脅大多是軍事方面的侵略,但在下一世代,由於科技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人類將面臨更大的危險。根據Joy的想像,並非只是將一把槍任意交給小孩,而是將一整個軍火庫任意交給狂人一般的危險比擬。在上個世紀,只有少數大型極權國家擁有毀滅性的武器;但隨著奈米科技、生化科技、機器人技術的發展,一些小團體甚至是個人都可能擁有終極的毀滅性能力,此時國家的約束力似乎太過薄弱。在這樣的時代中,要所有人都能夠清楚自己做任何事的後果以及人人成為愛好和平的世界公民的機率又有多大呢?對未來充滿不安的不只Joy,積極將晶片與人體結合的研究者Kevin Warwick則認為,在手臂植入晶片只是人類與機器結合的第一小步,依他的想法,機器不會消滅人類,但人類會變成機器,人類的意識將會被移植到極快速且歷久不衰的機器之上,生物性的人類將成為歷史,取而代之的是新種的機器—Cyborg。他說:這種混合體的價值迥異於人類,但這就是我們未來的方向。我知道這些聽起來太過科幻,但這是大勢所趨。此外,如我們所知,人類的滅亡似乎無法避免。[4]
此外,比利時恆星實驗室(Starlab)人工神經網路科學家Hugo de Garis,他正在創造自己設計的人工神經網路,他相信自己有一天終將成為「人工腦之父」,儘管他的研究將讓人工智慧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他認為,人工智慧一定會出現;但他也同樣相信,當創造出真正的高智慧物種時,人類將會後悔。
或許這會令人感到訝異,一些研究者致力於本身的研究,卻又預期這樣的科技將會將人類帶往難以預知的黯淡未來,似乎相當矛盾。就某種意義來說,這並非史上首次出現,原子彈發明人J. R. Oppenheimer第一次看到自己成果的試爆時,他說:物理學成了罪惡的來源。同樣的,再不同時代中,任何技術的發展都可能成為罪惡的根源。
相對於眾人的悲觀,當然也會有樂觀的看法。有「虛擬實境之父」稱號的Jaron Lanier在有人問及他,關於他的研究可能會對社會造成深遠的衝擊,但卻無法預料是怎麼樣的衝擊,他會不會感到恐懼時,他的回答是:因為遠距實境基本上是一種協助人類聯繫的工具,這個問題,其實在問一個人對人性應該樂觀到什麼程度。我相信,通訊科技提高了移情的機會,人類道德行為也會因而提升。所以我抱持樂觀的態度。…. [5]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機器人學家及人工智慧研究者Hans Maravec則認為,人類大腦比任何電腦都還要聰明,大腦內充滿了無數複雜的網絡連結,雖然如此,他同樣認為電腦的智慧或許會在2050年超越人類,這與Kurzweil的預期一樣,雖說現在最強大的電腦仍舊只有昆蟲的智力,但再五十年內機器人就可以從昆蟲進化至人類,Maravecu也與Warwick同樣認為人類會變成機器人,在他看來這些「後機器人」會是人類的後代。相對於之前的悲觀看法,同樣的演進,在Maravec所規劃的未來卻不是那樣地悲觀,他所看到的是人類可以將心智經由數位化的形式轉移至機器人之中,藉由數位實體的形式,在銀河系中擴散,以達永生的境界。
綜上所述,科技是否將會毀滅人類,抑或是為人類開展另一種永生的可能性,研究者與專家都有著不同的看法,也以無比的自信來為人類描繪未來的圖像。但唯一可以預知的未來事實,就是未來的不可預知性。
Herbert Marcuse在其著作《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指出,發達工業社會容易產生一種集體的意識,一種極度異化的的意識,高科技產物成了人類生活的靈魂,這是Marcuse所憂心的,他說:這是一種好的生活方式,一種比以前生活好很多的生活方式;但作為一種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礙著質的變化。[6]在其中存在著不合理中的合理性以及不自由中的自由,在富裕與自由掩蓋下的統治擴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領域,而使一切真正的對立一體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擇一致化,技術的合理性展現出它的政治特性,因為它變成更有效統治的得力工具,並創造出一個真正的極權領域,在此領域中,一切社會、精神和肉體都因此意識而恆久保衛這一領域。同樣的,新興科技的發展也正依附著人類不斷產生新的需要而前進,
當代工業社會是一個新型的極權主義社會,因為它成功地壓抑了這個社會的反對派和反對意見,壓抑了人們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從而使這個社會成了單向度的社會,使生活於其中的人成了單向度的人。造成其極權性質的主要動力在於無孔不入的滲透,技術的進步使社會可以在富裕與舒適的生活水平上,讓人們滿足於現況與未來的夢想,而願意放棄自由的追求或說是根本就不知自己已喪失了自由,也對自己將付出的代價渾然不覺。就如同《美麗新世界》中,人類不必奮鬥、渴望、感受痛苦、做艱難的抉擇…,也同樣不必過著任何有關傳統的生活形式,也沒有人會緬懷這些。但在同時,人類的生物性已經消泯,人性已被更動,社會也成了非自然社會。
在Marcuse看來,要從這樣的社會中得到解放是極為困難的,由於人們批判、否定的內心能力喪失已久,美麗新世界中的人不知道自己不具人性,重要的是人們根本不在乎人性是不是存在,整個社會已沒有能力提出任何的反對力量,這是一個沒有反對意見的社會。在Marcuse是如此,更何況是在這資訊與科技爆炸的時代之中,能夠存在的反對想法可能更被視為離經叛道,當時被認為是一種希望的弱勢群體也在現今同樣的集體意識中被「潛化」[7]了,即使是處在弱勢地位,心中所欲追求的,與一般群眾無異,更何況在強大科技力量之下,弱勢族群更是無力抵抗。此時,宣導成了最後的可能,社會學研究者肩負著「喚醒」的社會責任,
[1] Edward Tenner(2001),《科技反撲-萬物對人類展開報復》,蘇采禾譯,台北:時報。
[2] 來自捷克語robota,意指強迫性勞動。
[3] 引自Menzel,Peter&Faith D’Aluisio(2000),Robo sapiens:evolution of a new species,The MIT Press.
[4] 相關可參考Kevin Warwick Watch(http://www.kevinwarwick.org.uk/)。
[5] Jaron Lanier(2002),〈如臨現場〉,科學人雜誌,試刊紀念版,2002年一月,頁92-102。
[6] Herbert Marcuse(1996),《單向度的人》,劉繼譯,台北:桂冠,頁22。
[7] 意味著一種由外在進入內部的自動化歷程,過去人類經由社會化來形塑自己的人格,但現在卻可經由大眾傳播直接灌輸價值。